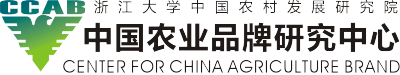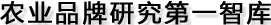公告栏:
站内搜索:
专著分享 | 地标品牌的治理路径
时间:2025-08-18 16:08:58 来源: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 作者:胡晓云 万琰 点击:853次

导语
2025年,由胡晓云主任和万琰博士主笔的最新专著《原型•文脉•现代化——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化》一书出版。本书对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化进行了全面地梳理阐述,通过16章的内容,分别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与探讨,并提供了作者与团队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成果。
我们将本书主要内容编辑成推文,陆续分享给大家。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地理标志农产品现代化发展的全貌,和品牌赋能的理论与实践。期望能与更多人一起,为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共同努力。
第八章,阐述了“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的治理主体及其路径”,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进行了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的治理主体、相关利益者、四种现存的治理路径级治理内涵的分析,提供了有关治理主体与路径的研究成果。第二节 地标品牌的治理路径。

鉴于与治理相关的概念众多且彼此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先按照应用领域的不同,将治理理论分为公司治理、品牌治理和公共治理三个部分,之后再详细介绍网络化治理这一具有多重含义、涉及多个研究领域的复杂概念。
地标品牌的治理路径
明确地标品牌治理主体,即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以及相对应的权、责、利关系,是分析地标品牌治理模式的基本前提,也是后续完善地标品牌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首要条件。
一、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文献中,伴随着美国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出现而兴起,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愈加得到学术界内外的充分重视452。现代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始于Berle和Means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对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研究。
根据古典经济学家所定义的企业制度,依附于所有权的收益权(或称剩余索取权,与所有权相对应的获取企业收益的权利)、控制权(包括剩余控制权、决策控制权和经营控制权)以及经营自治权是和合统一的,即所有者完全拥有上述的三大权利。但是,随着企业制度的不断发展演化,对企业拥有收益、对企业拥有权力、对企业行使权力的三项企业职能(分别对应收益权、控制权和经营自治权)及权利角色发生分离,公司的治理体制从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所有者主导的公司治理体制转向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经营者主导的公司治理体制453。由于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前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后者追求工资及工资衍生品最大化,因此,当公司经营者掌控公司之后,就有可能为追求个人目标而损害所有者利益。为解决此类因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与代理冲突,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代理成本的概念与理论应运而生454。公司治理的问题也由此展开。
进入20世纪80年代,相关研究进一步发现,Berle和Means笔下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在大多数国家并不普遍,但是却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相偏离的现象,即在金字塔控股结构下,终极控制股东可以用较少的现金流获得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而获得相对较多的利益455。这意味着终极控制股东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侵害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利益,侵蚀公司价值。至此,公司治理的目标实质上就是处理“股东-经理人”和“终极股东-中小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
公司治理的产生与公司制的企业组织形式紧密相关,并且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而愈加凸显其重要性。同时,企业的本质是通过签订长期契约,明确各利益相关方的权责利设置,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与交易成本的组织形式。因此,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与创新,以及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大量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公司治理的复杂程度逐步攀升,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围不再仅局限于内部股东与管理者,更扩展至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456,即,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457。笼统地说,可以从企业层面(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企业间关系层面(大型联合企业、企业集团)以及社会层面(法律、政治、文化、历史等)三个层面对公司治理予以分析458。
二、品牌治理
由于传统的品牌管理理念是基于品牌管理者与所有者权利上的彼此一致459,因此,一旦品牌组织形式发生较大变化,品牌产权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就可能出现产权模糊下权责利划分不清的问题。原本通过企业内部职权的协调以管理品牌资产的传统品牌管理模式难以对利益相关者施加有效影响,进而无法实现品牌的良性有序发展。由此出发,治理思想进入到了品牌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品牌治理(brand governance),探索如何通过保障由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品牌共建来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其中,以Merz和Hatch的观点较为主流460。
Merz等人通过梳理品牌逻辑的理论发展进程,指出品牌逻辑的进化经历了四个时代,分别以商品为中心的品牌时代(1900s-1930s)、以价值为中心的品牌时代(1930s-1990s)、以关系为中心的品牌时代(1990s–2000)和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品牌时代(2000年之后)461。在此基础上,Merz等人提出品牌价值不仅是通过公司与消费者之间孤立的二元关系所创造,而是通过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和社会互动共同创建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因此,公司应当确立一种有别于先前传统品牌逻辑下“公司-消费者”管理的全新理念,以应对利益相关者共创品牌价值这一“新的品牌逻辑(a new brand logic)”。通过对品牌发展状况的定期跟踪与诊断,探索、引导和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时调整营销决策,从而建立并维护牢固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关系,激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建。由于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创意味着公司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共享对品牌的控制权,因此被视为是“品牌治理”的议题462。
Hatch和Schultz也同样遵循品牌价值共创的基本假设与逻辑463。在他们看来,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组织的各部门都参与到了品牌的建设之中,并形成了一个利益结合体。利益相关者可以赋予并控制品牌的含义,并最终控制品牌为组织带来的价值,这就涉及到了品牌治理以及更大范围内组织治理的问题。
根据Prahalad和Ramaswamy的价值共创DART模型464,Hatch和Schultz在对话(dialogue)、渠道/获取(access)、风险(risk)和透明度(transparency)四个维度的基础上将完整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应用于品牌共创研究中465,构建了“2×2”的品牌价值共创整合框架:利益相关者/公司的参与(对话+渠道)与组织的自我披露(透明度+风险)466。对于前者而言,“对话”不仅可以发生在公司与消费者之间,还能够通过大量渠道与事件涉及整个企业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企业的管理人员、宣传人员、销售人员等能够共同参与到品牌价值共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容与反馈将用于指导品牌的建设,从而增加品牌与公司价值。后者指的是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对话、获取的次数越多,组织的透明度就越高,但风险也随之增加。这不仅是因为公司向利益相关者透露了相关内容,还因为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媒体、竞争对手等在内的许多其他人也建立了网络关系,这极大地增加了信息外泄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损害消费者体验、品牌声誉受损等风险的发生。然而与此同时,透明度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范围内的透明性,例如消费者需求、投资者立场、合作渠道信息等,能够为品牌发展带来可观的利益。考虑到透明度与自我披露所涉及的风险与益处相同,Hatch和Schultz以“组织自我披露”的概念来表述透明度与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与Merz等人侧重于分析品牌价值形成机理不同,Hatch和Schultz强调的是对品牌共创机制的探索,更关注在品牌控制权共享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对品牌共建过程中各品牌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与制度的设计,实现对相关利益者激励、监督、引导、制衡等有效控制,明确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有关品牌的权、责、利关系,进而保障品牌价值共创活动的合理有效运行。
综合双方观点,品牌治理意味着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建合作的情况下,对其行为模式予以管控的制度设计,以实现品牌价值共创过程的良性发展。
三、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理论界与实践界的重视。一方面,这来源于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欧盟等区域性组织的积极实践,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政府机构因过于臃肿而导致的管理失调、效率低下、财政税收危机、信任危机等一系列失灵问题,与市场机制分配不公、失业、市场垄断等失灵与公益缺失现象,需要一种新的调节机制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以更好地协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定位与互动关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面对公共管理中传统的层级制官僚行政模式与市场化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接连失效,西方学术与实践领域迫切需要以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应对社会公共诉求,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公共治理理论由此兴起。
作为治理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公共治理与政府治理、私人治理不同,是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公共治理的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除了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行为者都可以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实践中。政府与非政府的公共组织同为公共治理主体,地位平等,相互依赖与信任,通过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政府发挥的是“元治理”的作用;政府治理的主体虽然同为多元,但是更突出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是委托与代理关系;私人治理属于与公(公共事务)领域不同的私人领域,侧重从市场、企业部门的角度来理解治理467。
也有学者根据善治理论的逻辑演进,提出以“政府治理”为核心的理论和以“社会治理”为核心的理论分别为善治理论的1.0与2.0版本,“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理论则是善治理论3.0版本的主要代表,它强调“公共事务公共管理”。该观点将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认为“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468。新公共治理的主要提出者Osborne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将整个公共管理史划分为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三个模式与阶段,提出新公共治理是在一个多组织和多元主义的国家对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与结果,它能够将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整合嵌入到自身的范式框架之中,从而更好地应对21世纪公共政策执行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复杂现实469。Wiesel与Modell的后续研究证实了Osborne的观点,并总结了从公共行政模式到新公共治理的转变中出现的不同治理逻辑470。
截止目前,学界对公共治理的概念并未达成一致的定义。笔者将公共治理视为是治理在公共事务或公共行政事务领域中的应用,其公共性体现在(1)治理领域的公共性;(2)治理主体的多元性;(3)治理过程的公共性,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互相依赖和协作;(4)治理目标的公共性,强调公平、共赢以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与治理理论相同,公共治理理论也是一个理论丛林,包含了众多理论,例如“新公共服务”(New Public Service)、“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数字治理”(Digital Governance)、“公共价值管理”(Public Value Management)、“整体政府” ( Whole of Government ) 、“协同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水平化管理”( Horizontal Management)、新公共治理(New Public Governance)等。对于不同的国家与相关群体而言,“公共治理”有着含义上的区别与不同的说法,对于政府治理角色的定位也存在一定争议。不过当前学者们普遍认同,在公共治理的模式下,政府的职责将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需要相应让渡给公共机构、市场及社会第三方部门,由自治的行业协会、合作社、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来分担。通过改变传统公共行政的科层管理模式,建立起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上下互动、共同磋商、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机制,以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
四、网络(化)治理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日渐式微的背景下,针对科层治理导致的效率低下与市场治理导致公共性丧失等弊端,网络(化)治理理论问世,并在近年来成为了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为热门的术语之一,以及诸多学者笔下治理的主要模式之一。
“网络(化)治理”是一个较为综合与笼统的概念。事实上,社会科学中与“网络”相关的研究本就涉及多个学科与领域,概念多义,加之传入我国后传承的不同、翻译的偏差以及学者们的自行理解、修正与创造,使网络与治理的结合产生了多个学术术语,并且大部分学者对这些相近似的概念也没有加以区分,经常出现使用混乱的情形。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将网络(化)治理的理论来源分为三大类:第一来自于governing by network研究路径;第二来自于policy network(政策网络)研究路径;第三来自于前两者的综合,由于缺少明确的理论来源且数量较少,在此不过多介绍471。为避免混淆,笔者将前者称为“网络化治理”,后者称为“政策网络治理”。
(一)governing by network研究路径
网络与治理的结合最早出现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中,之后被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所仿效。因此,该研究路径下的网络化治理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是在工商管理领域的网络化治理,来自于国外的公司网络治理理论(network governs),第二是公共管理领域的网络化治理,其理论基本来源于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艾格斯提出的“governing by network”概念。
1、工商管理领域的网络化治理
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网络组织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司的生存空间、环境以及治理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根据Coase的企业理论,市场治理与科层治理被视为两种基本的匹配不同交易的治理结构与治理形式472。市场治理以节约交易成本为原则,科层治理则是以节约组织成本,尤其是代理成本为原则,通常而言是以股东利益至上,以层级组织的权威为依托的公司治理形式,属于企业内的制度安排。然而,在企业与市场的互动之中,不仅有市场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还存在一系列市场交换、组织机制与社会关系的共存并且相互渗透,兼有企业与市场某些特性的杂交形式,表现为双边、多边和杂交的中间网络组织形态473,企业间的经济活动就以网络组织为载体。学者Williamson在Coase交易成本分析理论的基础上,较早发现了这种在纯粹的市场和纯粹的科层制作为两极的连续统之间的其他组织形态,他将之称为组织的中间或混合形式474。
面对治理环境与治理方式的变化,西方学者开始对公司网络治理进行研究。Powell最早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提出(公司)网络治理是介于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中间、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独特治理形式,它既与科层和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又与之竞争475。Jones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认为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是一个有选择的、持久的和结构化的自治企业(包括非营利组织)的集合,这些企业根据隐性(implicit)或开放式(open-ended)的契约从事生产或服务,以应对多变的环境以及协调和保护交易,其中的契约是基于社会关系联结而非权威架构或法律性联结476。由定义可见,Jones所言的“网络治理”实质上就是对有别于市场与科层的“网络组织”这一新型组织形态进行的描述。
同样将网络治理视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国内学者李维安等认为网络治理中的网络内涵主要包括制度意义和技术意义上的经济组织或者经济主体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总和,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司契约以及基于价值观、习俗和道德等因素的东方文化关系、中国社会背景中的“关系”等众多的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477。网络治理就是指网络中所有结点有效合作的制度设计,包括对结点(网络主体)的治理、对结点间关系(关系强度与亲密度等)的治理、对网络整体(网络中所有结点或来自外部对网络整体的规范)的治理以及对网络内容(主体间传递的信息)的治理478。网络既可以成为治理的工具,又可以是治理的对象。全裕吉根据中间组织形态中市场原则、组织原则、社会关系的变化,将网络治理定义为“是对企业的单边治理与共同治理的扩展,是企业间各种关系安排方式和过程的总和,是使企业之间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网络组织中企业自觉遵循正式制度、规则和惯例的过程,更包括符合网络总体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479。
2、公共管理领域的网络化治理
进入公共管理领域,网络化治理不仅结合了公司网络治理理论、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管理学的系统和自组织理论,同时也在继承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作出了一定反思。
针对新公共管理下社会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网络化的“两化”现象,政府权力的“碎片化”以及重竞争轻合作、重部分轻整体的倾向,网络治理通过借鉴资源依赖、交易成本、社会网络、网络组织、供应链管理等多学科理论,试图弥合市场、政府、公司、社会之间的断裂,推动上述主体间的合作互动和良性竞争,实现政府内部运转的协调联动、政府—市场—社会的相互促进、政府政策行为的完整统一以及面向公众的无缝隙服务480。
其中,较早对网络治理进行完整论述的是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艾格斯,他们在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一书中提出“governing by network”概念,指出等级式政府管理的官僚制时代正面临着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网络化治理(governing by network),即一种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营利公司等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这象征着世界上改变公共部门形态的四种有影响的发展趋势正在合流:(1)第三方政府: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除了本身职责,或是引进企业力量外,也应纳入非营利组织参与;(2)协同政府:不断倾向于联合若干政府机构,有时甚至是多级政府以其提供整体化服务;(3)数字化革命:目前先进技术能够使组织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与外部伙伴进行实时合作;(4)消费者需求:公民要求更多地掌控自身的生活,要求在政府服务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要求政府的服务更加多元化,这些不断上升的需求正好与私人部门已经繁殖的个性化(特制的)服务供应技术相吻合481。另外,二人以“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两个维度,将政府管理形态划分为四种类型:“层级制政府”属于传统的官僚制政府形态,主要靠层级制权威进行着协调,因而治理效果不佳;“第三方政府”的公私合作程度较高,但政府对公私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低下;“协同政府”具有较强的网络管理能力,继而能实现有效的跨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仅限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网络化治理”既包含高程度的公私合作,同时政府又对公私合作网络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因此可以称之为跨界合作的最高境界482。
目前国内公共管理领域所探讨的“网络化治理”概念大多直接来源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艾格斯的研究,少数与之理解一致或以其为主。例如学者陈振明提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也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483。
(二)policy networks 研究路径
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分析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相互关系的一种解释途径和研究方法,在美、欧、英研究语境中各有侧重484。公共政策学界对于政策网络分析框架的准确起源并未形成一致意见,主流观点认为,政策网络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成长于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之后又逐渐在美国引发回应性研究485。沿着这条思路,可以将政策网络的相关文献划分为以下三个研究维度。
1、美国政策网络分析
美国学者基本定位于微观层次的研究,强调微观层次的不同机构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互动,而不是组织结构关系的互动。研究起初关注在美国政府机构、特殊利益游说组织以及对政府政策的特定职能领域具有管辖权的立法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之间较为常见的,封闭且相互支持的关系,Lowi形象地称之为“铁三角”(Iron triangle)486。Ripley和Franklin在“次系统”(sub-system)模型基础上发展出“次级政府”(sub-government)理论,认为次级政府就是在给定的实质性政策领域,有效地做出大部分常规决策的个体集群(clusters of individuals)487。典型的次级政府是由众议院和/或参议院成员、国会工作人员、少数官僚以及对政策领域感兴趣的私人团体和组织的代表组成。“铁三角”和“次级政府”的概念表明,某些公共政策是在一个由国会委员会、官僚体系以及利益集团所构成的封闭网络中建构的,参与者之间具有稳定的部门化关系488。
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Heclo在反思“铁三角”“次级政府”等概念的缺陷后,对政策次系统的本质予以重新定义和解释,指出多数政策议题的决策方式并非纯粹的“铁三角”模式,而是一个更开放的政策制定系统,即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s)。它比旧的“铁三角”概念包含了更多、流动性的参与者和更复杂的关系类型,是一个相对临时的、没有中央权威或权力中心的决策结构。因此,在议题网络中存在着大量且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预测的利益冲突,致使公共政策的相关问题更为复杂,难以达成有效共识,决策的结果也难以预料489。
2、英国政策网络分析
英国学者基本定位于中观层次的研究,重点研究在政策过程中,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之间的部门关系或者次级部门(sub-sector)结构关系对政策后果的影响。学者Rhodes是政策网络研究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一场多元组织基于交换关系的博弈(game),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参与者都在巧妙地利用各自在宪法/法律、组织、财政、政治和信息方面所掌控的资源谋取利益,寻求他们对政策结果的最大化影响,并且采纳了Beson对政策网络的定义,即“一群或复杂的组织因资源依赖而彼此结盟,又因资源依赖结构的断裂(break in the structure of resource dependencies)而相互区别”490。Rhodes将这种自组织的跨组织间网络视为英国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新的治理结构,是有别于市场和科层的第三种选择,其主要特征在于(1)公、私和第三部门之间相互依赖,以及组织间边界的改变与模糊;(2)资源交换和达成共识的需要,促使成员之间持续的互动与合作;(3)协商后一致达成的互相信任与博弈规则,是成员之间博弈式的互动的基础;(4) 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权。政策网络不对政府负责,而是自治、自我规范的。但是,尽管政府不享有特殊的支配地位,依然可以非直接、不完全地操控治理网络491。
早期英国学者遵循“结构-后果”的结构主义逻辑观,认为网络类型与政策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而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政策网络类型论。例如在Rhodes看来,政策网络表现为一个涵盖多种网络类型的连续统一体,两端网络结构的紧密-松散、封闭-开放程度不同,分别是强联结、高度整合的政策社群与弱联结、低度整合的议题网络,之间则是处于中间态联结与整合的,其他属性的政策网络。这些网络根据其成员组成、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成员之间的权力与资源分配,以及在整合性、稳定性、排他性等方面的差异,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专业网络(professional networks)、府际网络(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生产者网络(producer networks)和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s)五种类型492。
随着理论的演进发展,政策网络又产生了新的“行为-后果”的行为主义逻辑观,与先前的“结构-后果”分析逻辑相对应493。面对二者的争论,Smith和Marsh提出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之间并不是简单、单向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之间存在三种辩证或者互动的关系:(1)网络结构与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2)网络与网络环境;(3)网络与政策后果494。另外,英国政策网络分析也可以按照理论承袭的不同划分“美国流派”与“英国流派”,前者继承了美国政策网络研究的传统并承认其研究对英国的影响,例如Sabatier和Smith在Heclo“议题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倡议联盟”(advocacy coalition)的观点495;后者人数更多,以Rhodes为代表,他们认为政策网络的研究起源于英国,美国理论对于英国的国情与实践不具有适配性496。
3、德国、荷兰的政策网络分析
与英美学者研究传统不同,德国、荷兰的学者定位于宏观层次的研究,将政策网络用于描述和分析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视其为与官僚等级制、市场并立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形式与治理结构。
上世纪70、80年代,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为国家政策主体结构开始出现碎片化(fragmentation)、部门化(sectionalization)与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整个社会去中心化(centerless)的趋势也日益显现497,而政策网络的建立正是“对官僚制层级安排以及市场的局限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社会主体类型的扩大以及专门化的政策资源的分散在概念上的自然回应”498。这里的“网络”既与市场和科层模式有着交叉重叠的部分,又有差异之处,“是处于自愿与强制之间的一种中间体或揉合体” 499。
根据Klijn的观点,政策网络500描述的是通过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来审议、决策与实施公共政策。它基于公共、私人和公民社会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但却不一定平等的关系,并且通常与新的混合组织形式相关联,包括准政府机构、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多组织委员会,是一种更加分散、灵活且在某些情况下透明的议程设置、政策制定与执行501。
政策网络具有以下三点显著特征:(1)主体之间相互依赖。政策网络主体必须依赖其他主体以获得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2)政策网络是一个过程。政策网络就是各种主体利用各自资源,寻求实现各自利益和目标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3)政策网络的活动受到制度制约。政策网络主体因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和规则,这些关系和规则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主体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使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得以持续,使主体之间的资源分配的方式得以形成,并在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中逐渐发生变化502。
学者Börzel根据以上三个分析维度将这些国家的政策网络理论归纳为以英美学者为代表的利益调停学派(Interest Intermediation School),与以德国、荷兰学者为代表的治理学派(Governance School)。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将政策网络视为一个分析工具,主要通过分析部门与次级部门差异、公私行动者的角色以及非正式和正式关系来描述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过程中的互动情形,更加强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后者则将政策网络视为一种特殊的治理形态,即在政治资源分散于各种公共主体与私人主体时一种动员政治资源的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导治理模式,更加着重于公共管理领域503。
源于西方学者对于政策网络的争论,国内对政策网络的研究也分为分析工具与治理工具两个视角。前者多是以政策网络理论解释和分析我国某一政策领域中政策现象,例如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结果等;后者创造出“政策网络治理”这一概念,并将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应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当中。
五、地标品牌治理的内涵
(一)基于俱乐部产品的地标品牌治理
公共产品的理论由来已久,政府“守夜人”和个人“搭便车”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公共产品理论的古典渊源504。来自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德国的经济学家最先对公共产品展开了研究505。其中瑞典学派的Wicksell506和Lindahl507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入手,建立了公共产品供求的“Wicksell-Lindahl”均衡模型,现代公共产品理论也植根于此。之后,Samuelson真正对公共产品与私人物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其1954年发表的《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一文被认为是现代公共产品理论的奠基之作。
根据Samuelson的阐述,“每个人对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 goods)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相对而言,“普通市场定价适用于私人消费品(private consumption goods)”,即私人消费品能够加以分割,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照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人,并且“私人物品不具有集体消费品这一概念所固有的‘外部效应’”508。
在此基础上,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公共产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当一件公共产品被某一个人消费时,难以或无法排除他人也同时使用此产品。这意味着,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未付费者也能够同付费者一样从中获益。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某一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或影响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换言之,公共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与消费的边际拥挤成本为零,即,增加一个消费者并不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的增长,同时,增加一个消费者也不会减少其他人消费该产品获得的收益。
然而,Samuelson的经典定义将物品绝对划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产品”两类,忽视了在现实中大量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或“混合商品(mixed goods)”509。据此,Buchanan在Samuelson等人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于1965年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这一概念,填补了先前“二元化”理论成果在实用性与操作性上的空缺。
Buchanan提出俱乐部是一种组织,“是一种消费、所有权在会员之间的制度安排”510 。俱乐部仅对组织成员提供商品,即俱乐部产品,只有加入俱乐部才能获得产品的收益。同时,俱乐部设有排斥机制,产品的成本来自向俱乐部成员收取的费用(成本由所有成员共同分担),例如会员费,并采取某些措施阻止非俱乐部成员和不付费的成员使用其产品。
俱乐部产品并不代表介于纯私人物品到纯公共产品两级之间的所有产品,它必须具备足够的排他性(对外)和一定的竞争性,非竞争性但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以及存在拥挤效应但无排他性的公共产品都不是俱乐部产品。
俱乐部产品由成员平等、共享使用,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竞争性,边际成本为零。但俱乐部成员的最优数量是有限的,俱乐部产品在共享范围之外存在着拥挤效应,当俱乐部会员超过最优数量时,后续增加的会员量将降低原本会员的效用。为获取个人均衡和俱乐部均衡,俱乐部必须要同时确定俱乐部所应提供的最优俱乐部产品量与应容纳的最优会员数511。
对于地标品牌而言,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地理标志的使用必须要符合特定条件,具有排他性;在一定范围内,某一地标品牌使用人的数量增加并不会使地标品牌产生额外的生产成本,也不会降低其他使用人的收益,具有非竞争性;地标品牌具有明显的“声誉外溢”效应,能够广泛惠及原产地以及所有品牌使用人,其社会效益超出了参与地标品牌生产经营的公司的利润,能够产生正向的外部性。因此,地标品牌属于俱乐部产品的范畴,是一种由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加工者所构成的俱乐部会员的本土化资产512,不仅具有治理的必要性,其治理也体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地标品牌治理具有不容忽视的公共价值取向,以增进和实现公共价值与公共利益为核心诉求,更注重治理效率而非经济效率,并且涉及一系列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2)政府公共部门始终是地标品牌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地标品牌治理离不开政府持续的支撑、合理的引导以及有效的协调。在一定情况下,政府的强势介入与干预也尤为必要;(3)基于地标品牌对内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品牌治理过程中,极易面临“搭便车”“囚徒困境”“劣币驱逐良币”等潜藏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4)由于地标品牌具有外部效应,因此当品牌治理处于良性态势时,能够产生区域光环、产业集聚、规模经济等正面的溢出效应,反之,则可能造成“公地灾难”等一连串负面效应。
(二)基于网络形态的地标品牌治理
网络是一个较为抽象且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境里含义差别巨大。在社会学领域,“网络”大多是指连结一组人、物或事件的特殊关系形式,存在于网络中的一个人、事物或事件,可以被称为行动者或节点513。英国人类学家Brown最早提出了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的概念514,之后由Wellman发展成熟,他认为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s)可以由网络(networks)的形式所展现,即一系列结点(nodes)以及描述结点间互相关联的一系列纽带(ties)。结点是社会系统中的成员,可以指个人,也可以代表团体、公司、家庭、民族国家或其他类似的集体。纽带代表着资源的流动、对称的友谊、传输转移,又或是结点之间结构化的关系。换句话说,由这些社会成员和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social ties)或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所构成的结构就是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515。可以看到,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社会网络的概念超越了人际关系的范畴,网络的行动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单位,如家庭、部门、组织516。在社会学和公共性质学的话语体系中,“网络”可以看作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或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517。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由于经济交换的社会嵌入性,任何经济活动都已然处于广泛的关系网络之中,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会互相“溢出”,企业之间的交易也不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涉及同质或异质的企业、客户、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等多个行动者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介于市场与科层结构之间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网络组织”。其中,社会网络能够通过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方式影响经济活动的秩序、进程与结果518。关系嵌入体现在双边或多边交易的质量、深度、共识度、信任程度、信息交流等方面,结构嵌入可以看作是双边交易的扩展,即行动者之间可以“通过与第三方的间接连接而形成以系统为特征的关联结构”519。同时,社会资本也能够以嵌入性在网络组织中生产、链接与流动。网络组织在实践中有许多具体形式,例如战略联盟、企业联合体、虚拟组织等。可以说只要是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跨界经济联合,都可纳入网络组织的研究范畴520。这里的“网络”一词具有三重含义,分别是社会关系层面的网络,组织结构层面的网络以及信息技术层面的网络。
网络化组织模式不仅深刻改变了公司的组织结构与经营模式,也在不断渗透、影响各行业以及政府传统的层级组织与管理模式。随着企业加快集中向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组织界限越来越模糊,而市场化改革在分权与削弱政府的同时,也让众多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自组织接连涌现。由此,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得以重塑,主体间的界限与责任越发模糊,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得以形成。
事实上,碎片化、部门化、分权化甚至是“空洞化”的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早已缺乏足够的计划、执行与调控能力,加之网络技术的发展与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的多元化、去中心化与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更是愈加凸显。在此情境下,传统官僚制既难以具备解决公共事务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工具、资源和能力,也无法单独完成管理复杂公共事务的任务,亦或是全方位主导治理活动,必须依赖外部环境、寻求多方合作,通过充分联结、调动、协调来自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力量的共同参与,在网络化的结构与机制中实现自我治理与公共价值的最大化。
因此,尽管学界在“公共治理”的定义上未达成共识,但对其网络形态的认同毋庸置疑,通常将网络视为一种处于市场、层级官僚体制之间并优于二者的组织形态。它不是建立在行政的权威关系或市场的契约关系之上,不同于传统的政府干预与市场资源配置,而是以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交换为基础,各参与主体之间存在资源与利益的依赖关系,但同时也因理性与策略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其行为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程度也大幅提升,存在多治理主体之间目标诉求不兼容等问题。另外根据治理目的的不同,网络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政策网络、多层治理网络、伙伴关系以及集群网络、供应链网络等。
地标品牌作为一种“准公共品”,其治理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介入。但同时,地标品牌更是一个开放性的网络系统,涉及个体农户、农企、合作社、行业/产业联盟、协会等众多的生产经营主体和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科研院所等组织机构,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维度也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性。品牌各主体之间既横向合作又纵向相关,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博弈。地方资源与品牌建设之间既互为支撑、彼此成就,稍有不慎,又可能“一损俱损”。
所以,地标品牌不仅具有治理的必要性,而且具有更为复杂的治理内涵与治理问题,势必会面临不同于公共管理、公司治理以及品牌管理模式的网络治理挑战,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以一见:
(1)主体复杂:正如上述所言,地标品牌治理是由多元主体构成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宏观上连结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领域,微观上品牌在创建、投入使用、收益、处置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责任与权利,由政府部门、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公民个人等若干个机构或成员共同承担和拥有,全体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共享风险与回报。这意味着品牌的产权归属更为复杂,产权主体不明晰的问题亟待解决。同时,品牌各主体潜在的差异化利益诉求也有待协调和整合;
(2)机制复杂:品牌治理各主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市场机制)、行政权威的命令(行政机制)、社会关系的嵌入(社会机制)以及共同遵循的规则(组织机制)构建和参与治理网络。各主体之间具有合作、冲突、竞合、博弈等多种联结与互动关系,并且可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例如处于网络核心的强势政府与网络边缘的弱势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具有资源优势的龙头企业与资源劣势的个体农户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品牌有赖于协商、激励、约束、学习、信任等多样化的治理机制共同维护治理网络的运行;
(3)结构复杂:地标品牌治理不再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单中心主义”,也打破了传统企业组织机构的界限与层次,呈现出多主体、多中心、多层次横纵联结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同时,由于地理标志产品的地域性和风土特征,地标品牌具有以血缘、亲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大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区域独有的文脉、传统、惯习、记忆等也附着于社会资本嵌入其中,共同对地标品牌治理网络的形成与运行施加无形的影响。
综上可知,地标品牌治理颠覆了以政府治理为主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和以市场化治理为主的新公共管理范式,也有别于传统的基于企业内部职权设立的品牌管理模式,而是在一个结构化与关系嵌入的网络下,来自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包括企业组织、中介组织、消费者个人等)的多元化品牌利益相关者按照一定的制度与合约规定,为追求具有公共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展开的协同行动,即用“网络”来治理;同时,地标品牌治理也意味着对品牌各利益相关者行为模式予以管控的制度设计,通过建立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机制,实现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引导、激励、协同、监督、制衡的有效控制,明确地标品牌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配置,从而推动品牌治理网络的良好运行、品牌决策的科学化以及地标品牌公共利益与公共效用最大化,即对“网络”的治理。
参考文献:
452 姚云、于换军:《国外公司治理研究的回顾:国家、市场和公司的视角》,《金融评论》2019年第3期,第92-109页、第126页。
453 关鑫、高闯:《公司治理演进轨迹与问题把脉:基于“两权分离”与“两权偏离”》,《改革》2014年第12期,第107-117页。
454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4): 305-360.
455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2): 471-517.
456 严若森、贾伟娟:《人性假设与公司治理:“治理人”假设的提出》,《人文杂志》2015年第1期,第45-51页。
457 李维安《公司治理学 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7-13页。
458 陈仕华、郑文全,《公司治理理论的最新进展: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第156-166页。
459 王彦勇、苏奕婷,《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品牌治理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35-140页。
460 王彦勇、徐向艺,《国外品牌治理研究述评与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35卷第1期,第29-36页。
461 Merz M A, Yi H, Vargo S L. The evolving brand logic: a service-dominant logic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9, 37(3): 328-344.
462 Ind N, Bjerke R. Branding governance: A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o the brand building process[M].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2007.
463 Hatch M J, Schultz M. Toward a theory of brand co-creat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brand governance[J].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2010, 17(8): 590-604.
464 Prahalad C K, Ramaswamy V. The future of competition: Co-creating unique value with customers[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4.
465 在此之前,虽然学者们注重将所有利益相关者视为品牌的共同创造者,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只考察了消费者与营销人员。
466 同15。
467 韩兆柱、翟文康:《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23-39页、126-127页。
468 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第58-61页。
469 Osborne S P. Introduction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 [M]// Osborne S P.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Governance.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0: 1-16.
470 Wiesel F, Modell S. From new public management to new public governance? Hybrid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sector consumerism[J].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 Management, 2014, 30(2): 175-205.
471 田华文:《从政策网络到网络化治理:一组概念辨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49-56页。
472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meaning[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1988, 4(1): 19-32.
473 彭正银:《网络治理理论探析》,《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3期,第51-55页。
474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42.
475 Powell W W.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12:295-336.
476 Jones C, Hesterly W S, Borgatti S P. 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 Exchange conditions and social mechanis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22(4):911-945.
477 李维安、周建:《网络治理:内涵、结构、机制与价值创造》,《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61-65页。
478 李维安、林润辉、范建红:《网络治理研究前沿与述评》,《南开管理评论》2014年第17卷第5期,第42-53页。
479 全裕吉:《从科层治理到网络治理:治理理论完整框架探寻》,《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第44-47页。
480 刘波、王力立、姚引良:《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5期,第140-146页。
481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孙迎春译:《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9页。
482 同上,第3页。
483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484 孙柏瑛、李卓青:《政策网络治理:公共治理的新途径》,《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5期,第106-109页。
485 胡伟、石凯:《理解公共政策:“政策网络”的途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7-24页。
486 Lowi T J. American business, public policy, case-studies, and political theory[J]. World politics, 1964, 16(4): 677-715.
487 Ripley R B, Franklin G A. Congress, the bureaucracy, and public policy[M]. Homewood, Illinois: Dorsey Press, 1980: 10.
488 Jordan G, Schubert K. A preliminary ordering of policy network label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2, 21(1-2): 7-27.
489 Heclo H. Issue Networks and the Executive Establishment[M]//Young R, Binns C, Burch M, et al. Introducing government: a read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4-212.
490 Rhodes R A W. Policy Networks: A British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0, 2(3): 293-317.
491 Rhodes R A W.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J]. Political studies, 1996, 44(4): 652-667.
492 Rhodes R A W, Marsh 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cy network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2, 21(1-2): 181-205.
493 同37
494 Marsh D, Smith M. Understanding policy networks: towards a dialectical approach[J]. Political studies, 2000, 48(1): 4-21.
495 Jenkins-Smith H C, Sabatier P A. Evaluating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94, 14(2): 175-203.
496 朱亚鹏:《西方政策网络分析:源流、发展与理论构建》,《公共管理研究》2006年版,第204-222页。
497 Guilarte M, Marin B, Mayntz R. Policy Net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7(3): 295-530.
498 Kenis P, Schneider V. 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analysis: scrutinizing a new analytical toolbox[M]//Marin B, Mayntz R. Policy net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Frankfurt a. M.: Campus Verlag, 1991: 25-59.
499 鄞益奋:《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1期,第89-96页、第126页。
500 Klijn在原文使用的是“governance network”(治理网络),为理解方便,笔者使用“政策网络”一词予以代替。
501 Klijn E H, Skelcher C. Democracy and network governance: Compatible or no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7, 85(3): 587-608.
502 Klijn E H. Analyzing and managing policy processes in complex networks: 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policy network and its problems[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6, 28(1): 90-119.
503 Börzel T A. Organizing Babylon—On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8, 76(2): 253-273.
504 王爱学、赵定涛:《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回顾与前瞻》,《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第38-43页。
505 Pickhardt M. Some remarks on self-interest, the historical school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public goods[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005, 32(3): 275-293.
506 Wicksell K. Ein neues Prinzip der gerechten Besteuerung. Finanz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M]//translated to English as “a new principle of just taxation” by Buchanan J M and reprinted in Musgrave R A, Peacock A T(Eds.):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58: 72-118.
507 Lindahl E. Die Gerechtigkeit der Besteuerung: Eine Analyse der Steuerprinzipien auf Grundlage der Grenznutzentheorie[M]//translated to English as “Just taxation-a positive solution” by Henderson E and reprinted in Musgrave R A, Peacock A T(Eds.):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58: 168-176.
508 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6(4): 387-389.
509 Snidal D. Public goods, property right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79, 23(4): 532-566.
510 Buchanan J M.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J]. Economica, 1965, 32(125): 1-14.
511 张宏军:《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溯源与前瞻——兼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设计》,《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20-124页。
512 Benavente D. The economic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Gis modeled as club assets[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2010.
513 张康之、程倩:《网络治理理论及其实践》,《新视野》2010第6期,第36-39页。
514 Radcliffe-Brown A R. On social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40, 70(1): 1-12.
515 Wellman B, Berkowitz S D. Introduction: Studying social structures[M]//Wellman B, Berkowitz S D.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4.
516 王夏洁、刘红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知识链分析》,《情报杂志》2007年第2期,第18-21页。
517 陈剩勇、于兰兰:《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8-119页。
518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 510.
519 同25。
520 孙国强:《网络组织的内涵、特征与构成要素》,《南开管理评论》2001年第4期,第38-40页。